在甲骨卜辭中,常常出現這樣的句式:『……,用。』或者『……,茲不用。』在這裡,用與不用出現在命辭之後,表示對命辭內容可施行與否的裁定。這大概就是【說文解字】中說『用,可施行也』的原因。但這其實是用的引申義。 用,甲骨文字形就好像一個平時用的桶,乃桶的初文。一般是用三豎表示桶的軀幹,其中穿插的橫線表示桶箍,器無定形,故字無定式,橫線或多或少,或上或下,或正或斜,形成了甲骨文中寫法不一的『用』。到西周,寫法基本統一,小篆字形就是承此而來。因為桶是日常用器,用便引申為一切器用之用;桶可以使用,所以用引申出了使用、實用、任用、施用等等意思來。 多友鼎拓片
『用乍(作)寶尊彝』、『子子孫孫永寶用』,是青銅器上最為常見的銘文之一。前者說將這件青銅器作為禮器使用,後者說希望子子孫孫永遠都能保存着這件器物。這都是因為這些青銅器一般都具有重要意義,與其功勳有關。比如西周晚期的多友鼎,記載着當時與獫狁的一場戰爭,獫狁入侵,多友率兵迎擊,取得了勝利,周王也重賞多友,賜給多友青銅一百多鈞,多友鑄造了這個鼎以紀念這件事情。青銅器的不朽,刻錄功業的不朽。古人希望這些器物能夠永世流傳,也希望後世子孫能永遠銘記、珍惜祖先的功德與榮耀,並激勵自己努力奮鬥。這裡的用,承載着功勳與希望。 用這個字的內涵,無限延伸。明清之際,王夫之、黃宗羲、顧炎武等思想家,提出了經世致用一說,認為學問須有益於國事,要將所學用到解決社會問題、維護國治民安上來。事實上,這一思想內涵早已形成。商周時期,官學就強調人才培養和知識傳授,是為了天下社稷的興盛與安寧。周代的官學由官吏擔任教師,將政事與教育合一,要求學生要掌握禮樂射御書數六種基本技能,培養文武兼備之士。春秋後期私學興起,但政務的管理依舊是其教授的重點,孔子教學重在教人學為人之道,但也涉及了很多為政之道。 所以,經世致用的用,充滿了社會意義。在經世致用的思想下,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,有着治國平天下的信念,自覺擔負起關心時事、為國效力的使命,心懷天下,心系蒼生。無論是教育、學術、文化乃至個人修身,最終都是為了用,最後都歸結到『經世致用』上來。 經世致用的用,要用在為天下、為國家、為民族上,要用在匡時濟世上,這就將國家、民族和個人融合在一起。古代的經世致用之學認為,做人和做學問,二者是統一的,並且前者比後者更為重要。人要有高尚的人品,要有氣節和操守,特別是在國家民族這些大節上不允許有污點,不然經世致用也就失去了靈魂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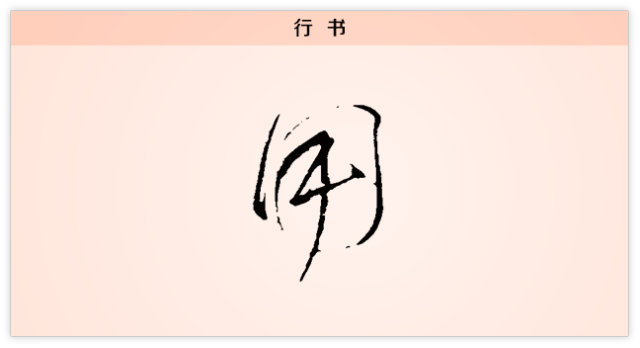 世事無絕對,但人應當做一個有用的人。自立自強,謙卑謙遜,敢作敢當,發揮作用,為社會做出貢獻。(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施希茜) |
